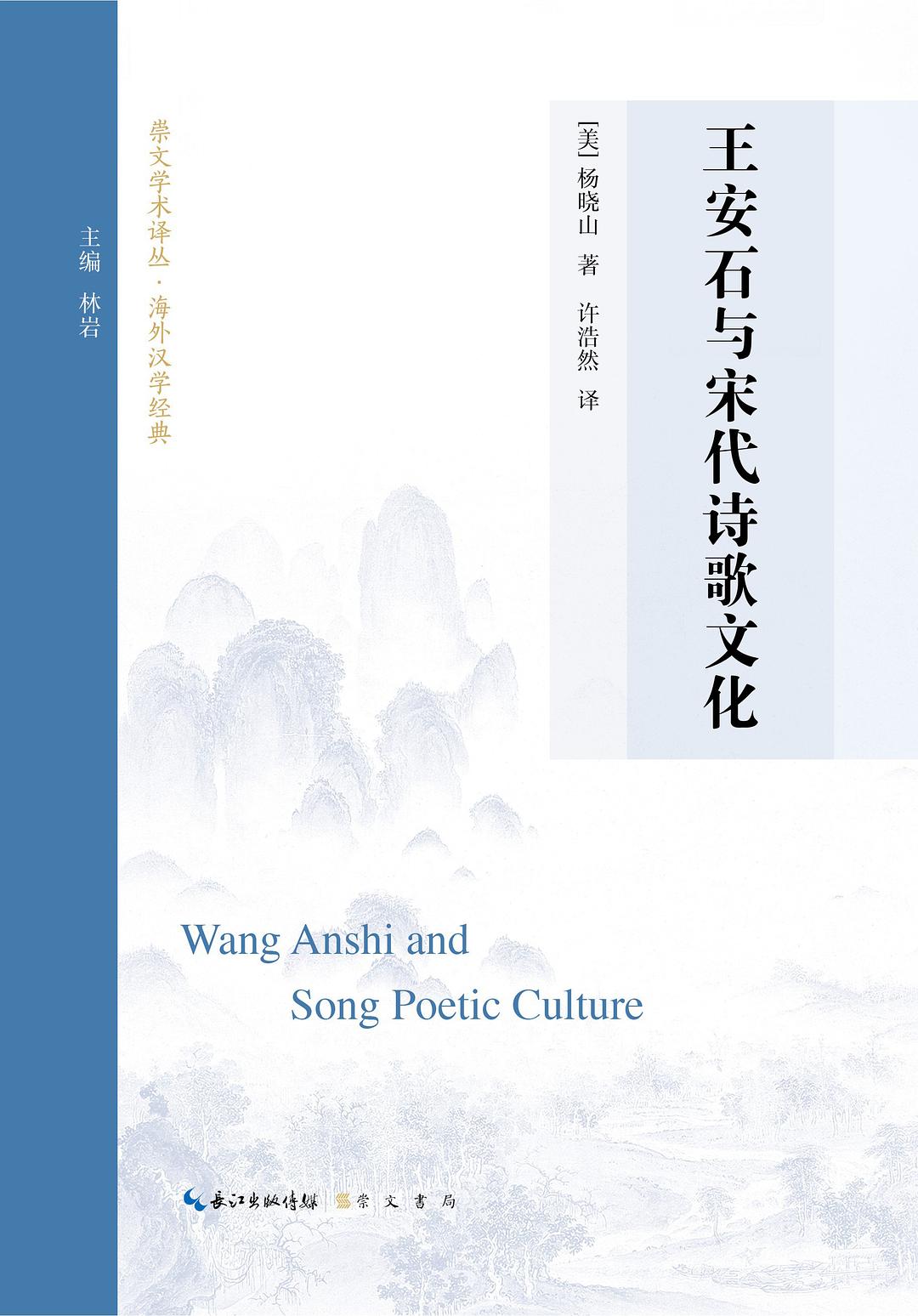
[美]杨晓山著,许浩然译,崇文书局2024年3月出版,360页,88.00元
当代的研究者们应当不会否认,王安石有实力跻身于宋代顶尖诗人的名单之中。可怪的是,在宋诗研究新见迭出的当下,王安石诗歌的研究进展仍显得十分缓慢。尽管近年已经有了《王安石全集》(王水照,2016)、《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2018)、《王安石文集》(刘成国,2021)、《王安石诗笺注》(董岑仕,2021)等一系列诗文系年和文献整理领域高质量的基础成果,可面对王安石的诗歌文本,研究者的目光似乎很难跳出佛禅思想、晚期风格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已经被高度关注的问题。这当然能够说明这些问题在王安石诗歌研究上的重要性,但如何在这些问题上推陈出新,并生发出更多的话题,恐怕是所有王安石研究者共同面临的困境。

王安石像
杨晓山教授2021年出版的《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可以看作当下研究者对这一学术困境的回应。本书经许浩然先生翻译,于2024年3月由崇文书局出版。该书共五章,每一章都考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这五个独立问题又统摄在一个更宏观,也更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下,即王安石在宋诗史上的定位。
第一章《〈明妃曲〉:唱反调的诱惑与危险》重新梳理了王安石《明妃曲》由宋至清的批评史。相比于此前内山精也先生的力作《王安石〈明妃曲〉考》(1993年,1995年,中译本2005年),本章在《明妃曲》批评史的谱系上补充了元至明的四条重要史料,包括了刘辰翁、赵文、顾起元、谢肇淛的评价,参合本章与内山氏的论文,基本可以勾勒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王安石《明妃曲》批评史。此外不同于内山氏前作的是,本章最终的落脚点不在于神宗朝士大夫意识形态的转关,而在于宋诗“翻案”风气的文化意涵。作者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明言:“宋诗的翻案倾向标志着一种愿望,即通过刻意指斥传统观念、反驳既定见解来标新立异。”(中译本,60页)从这一结论当中,我们能看出作者试图将王安石回置到唐宋诗歌发展史中的努力。在作者看来,当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被放到唐宋翻案诗的传统之中后,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就自然地浮出水面:“假如说翻案诗法是宋代的一种风尚,而王安石那些耸人听闻的诗句只是这一风尚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些诗句何以会引发如此之大的争论呢?”(60页)作者的解释是,一方面,王安石的言辞越过了道德规范与雅正品味的界限;另一方面,读者在政治、道德上对王安石抱有成见。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与内山氏一样举出了王安石前后同样涉及华夷之辨的昭君诗,其中包括内山氏引用过的晚唐王叡《解昭君怨》和吕本中《明妃》诗,也包括了晁补之《题伯时画》、韩驹《题伯时画昭君图》。作者指出,这些作品并没有像王安石“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一样受到同时人乃至后世的严厉批驳,这应当能够解释在宋诗主张翻案求奇的整体氛围下,王安石独独受到猛烈攻击的特殊现象。
作者用王安石“爱唱反调”的个人气质引向了本书的第二章《〈唐百家诗选〉的传统与个性》。这一章关注的是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去取标准的公案,试图回应《唐百家诗选》不选李杜等大家是否由于王安石的偏执个性问题。不同于第一章以梳理批评史为主的纂组方式,本章亮出了鲜明的观点,即王安石编选的“遗漏”应当来自其参考文献的限度,且不选大家的选本特质也并非王安石刻意的标新立异,而仅仅是唐人选唐诗传统在北宋前期的延续。前一结论的得出得益于作者对《唐百家诗选》编纂公案的细密梳理,作者辨析了历来对《唐百家诗选》不选大家现象的诸种解释,包括“有意为之”“条件有限”以及“大家别集易得”三种。从逻辑上看,第三种理由本应被归入第一种,但特别的分立确实有利于作者的驳论。在三种观点中,作者明显倾向于第二种,并且花了大量笔墨驳斥了第三种。作者驳斥第三种观点的依据是,在《唐百家诗选》编成之前,唐集仅有杜甫、韩愈、柳宗元、薛能、贯休五家已有可考之刊本,且杜集刊刻仅在《唐百家诗选》编成一年之前,刊于吴门的版本又未必能快速流布至京师,故王安石能利用的主要还是宋敏求家藏的旧抄本。复因为宋敏求校订过的诸家别集中有不少并未被《唐百家诗选》所取,故而作者推测:“宋敏求提供给王安石的只是其家藏书的一部分……王氏选本中明显的阙失并非反映了他的某种编纂意图,而更有可能是外部条件所致。”当然,作者也坦承对这一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这一番论证未必确凿,但作者对后一结论的分说则相对有力地回应了《唐百家诗选》不选大家是“自有微旨”的传统认识。这一结论的得出与本书整体的研究取径直接相关。作者没有粗暴地将王安石理解为“一个孤立的大诗人”(280页),而是时刻力图将王安石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趣味置于唐宋诗歌转型的长线索之中。作者指出,不选李、杜、韩三大家的做法在唐代的唐诗选本中相当常见,甚至宋元人编纂的《二妙集》《注解选唐诗》《唐音》等不同体例的选本也不以李、杜、韩为诗作去取的唯一尺度。如此看来,在唐宋诗学转型的长线索中,《唐百家诗选》的标准并没有十分独特,反而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足以见出宋代诗歌经典化的发展历程。
王安石的晚年诗历来是王安石研究的重点,本书第三章《晚期风格》也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相较于前人的研究,作者独具匠心之处在于将“晚期风格”视为一个唐宋诗学中的延续性问题,从而将王安石看作“晚期风格论”在唐宋诗歌转型中的个案之一,而不是孤立地讨论王安石晚年诗的风格本身,这种写法显然又紧扣了本书为王安石寻找诗史定位的核心诉求。王安石晚年诗研究的一大困境便在于王诗编年的不确定性,历来讨论王安石晚年诗的研究者大多将荆公集中精严工丽的绝句视为其晚年诗的代表,但这些作品的系年并不容易,即便是能确定为王安石罢相后作于江宁的作品,也很难辨析其中哪些写于熙宁七年四月至次年二月,哪些写于熙宁九年第二次罢相之后。这种编年上的困境很大程度来自于王安石前后风格的一致性,对于这一问题,莫砺锋教授《论王荆公体》(《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早已揭橥,莫文认为王安石“对于诗歌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是从早期就开始的”,并从用字押韵、对仗、用典等角度列举大量作品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看来,正面地对王安石晚年绝句精工雅丽的风格反复分说往往容易堕入循环论证的陷阱。而本章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被视为一个诗学问题的脉络,从而再一次由王安石个人诗风的“小结裹”引向了唐宋诗歌转型的“大判断”,也就巧妙地避开了研究王安石晚年诗时循环论证的困境。作者先是经由编年本杜甫集的出现点明了“晚年风格”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产生,从吕大防论杜、韩“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言论出发,引向了黄庭坚对杜、韩晚年“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评骘,继而梳理出了十二世纪以降胡仔、朱熹、陈善、魏了翁、刘克庄、方回等人对杜甫、苏轼、黄庭坚、陈与义晚期风格的批评谱系。如此,当作者将宋人对王安石晚年诗的关注纳入这一谱系时,那些被视为王安石晚年作品的绝句系年是否准确就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王安石晚年近体诗风格是否真的有极大的转变也可以悬置不论,重要的是,两宋之际的批评家已经坚信,王安石和杜甫韩愈一样,在晚年发生了风格转变,且其晚年诗远胜于早年。“晚期风格”在西方学术史上通常用来评价美术或音乐家晚年风格的转变,作者将这一视角引入中国文学批评也并不突兀,毕竟本章已经罗列了充分的史料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这一话题的固有存在。由于艺术家晚年身体的衰落和技艺的浑成,其晚年作品大多轻视技巧而注重自然,作者引述格尔格·西默尔(Georg Simmel)的话:
(晚年艺术家)已不再讲究形式的严谨以及感性的魅惑,也不像以往那样全神贯注于身边的万事万物。他们的作品中剩下来的只是一些粗犷的线条,而这些正是他们的创造力最深刻、最切身的迹象。(第185页)
这与杜甫“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黄庭坚“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表述何其相近。当然,作者也指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晚期风格论的独特性,即适用对象的局限,相比于原始语境中对艺术、音乐作品的评价,中国本土的晚期风格论仅被用于狭义的诗、古文以及书法,尚未看到关于美术、音乐甚至小说、词、骈文等其他文体的表述。而仅就王安石来说,如果承认宋人对王安石晚年风格转变的认识,荆公晚年诗精严巧丽的作法也和西方晚年风格论粗犷随意的判断有极大的差别。对于这一现象,今后或许还值得更深入的探讨。尚应提及的是,本章是作者此前《论宋代的晚期风格理论》一文的改写(见收于《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相比于前作,本章调整了一些段落的顺序,增补了部分史料,对部分内容也有所删减,比如文章最后涉及疾病与死亡的一些表述。在论及中国古代文人因疾病而转变人生观的现象时,作者举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例子,这段文字关涉的实则是发愤著书的问题,与作品的晚年风格无关,作者在本书中删去这段文字,也应当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四章《从寒山到钟山:佛理与诗法的简短巡礼》篇幅虽小,但给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论断,即王安石在寒山诗拟作传统中的节点作用。四库馆臣评价寒山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寒山子诗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已然为寒山诗的风格立下了切中肯綮的判断,项楚先生也用“或俗或雅”总结了寒山诗的两种基本风格。值得指出的是,研究者在讨论寒山体的风格问题时,往往仅将将工、庄和率、谐共时性地并举,极少注意到寒山体两种风格的历时性转换。本章对此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即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正是寒山诗拟作风格“由抒情描写之诗转向了讽刺说教之诗”的转折点。作者认为,此前清凉泰钦、汾阳善昭、雪窦重显的拟作都偏向寒山诗雅洁幽静的特点,语言上并不具有明显的口语性,且全诗以写景为主,不带有强烈的说教气息;而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则以口语性、说教性为主要特点,少有典雅的语言和清幽的意象,这一传统此后直接被北磵居简、慈受怀深等禅师与曹勋等士大夫继承。从现存唐宋拟寒山诗的写作实态上看,这一判断应当是准确的。现存唐宋拟寒山诗的数量并不甚夥,加之如今检索工具的便捷,得出这一判断并不十分困难,而此前研究者未能关注到这一现象,当是因为没有将拟寒山诗视为唐宋诗歌转型线索中的一个特别问题来看待。本章的结论,再次见出作者研究视角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本章并未解释一个关键问题,即王安石何以成为拟寒山诗谱系中的风格转捩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寒山诗中偏向白话说理的作品可以作为禅僧升堂说法时的话头,如《古尊宿语录》载风穴延沼法师上堂时,即举寒山诗曰:“梵志死去来,魂识见阎老。读尽百王书,未免受捶栲。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古尊宿语录》卷七)《宝觉祖心禅师语录》载晦堂祖心升堂时亦举寒山诗云:“我闻释迦佛,不知在何方。思量得去处,不离我道场。”而王安石居江宁期间醉心佛禅,当有听法经历,其诗《书定林院窗》有“道人今辍讲,卷祴寄松萝。梦说波罗密,当如习气何”之句,可为一证。认为王安石是在听法过程中对寒山诗的白话、说教传统产生兴趣,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王水照先生曾将文学与党争称作宋代文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第七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2011年),而王安石作为北宋党争的核心人物,其诗歌与党争的关联自然不应被轻易放过。本书第五章《〈君难托〉:类型惯例与党派政治》就巧妙地选择了王安石的乐府诗《君难托》作为个案,讨论了王安石诗在北宋党争语境中被阅读、阐释的过程。《君难托》很少被研究者用来专门讨论,但这首诗在王安石身后的确引起了一桩值得关注的公案,即本诗的作者归属问题。作者从李壁注文中“此诗恐作于神考眷遇稍衰时,然词气殆不类平时所为”的直觉判断引向了宋人对《君难托》一诗归属的质疑,进而梳理了此后批评家对此诗寓意的索隐。认为《君难托》寓有微旨的观点不仅影响了宋代的批评家,当代的学者仍有持此论者(如杨隽《臣妾意识与女性人格——古代士大夫文人心态研究之一》,《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但对于这一问题,实则如作者所说:“王氏本人写作该诗是否真有此寓意(甚至他是否写过该诗),抑或以此寓意来解读该诗是否合理,这些问题皆不重要。”重要的是,宋代的批评家为何相信这首诗有寓意,且反映的是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先是梳理了中国的弃妇诗传统,说明以夫妻关系映射君臣关系在宋代是自然的,转而又点明了《君难托》的阐释史在弃妇诗传统中的特异性,即批评家为这首诗添附政治意涵并不是为了提高这首诗的价值,反而是为了诟病王安石的不合臣节。作者试图用北宋的党争语境来理解这一阐释上的差异,作者认为,北宋庆历以来的朋党之争催生了一种“构陷性”的诗歌阐释新传统,王安石本人也未能逃脱这一新传统的控制,这使得弃妇诗的政治比兴传统被负面地利用,成了王安石“谤讪宗庙”的罪证。作者的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新奇,内山精也《“东坡乌台诗案”考》一文对这一问题已有更为深刻的论述。本章的贡献在于用更多的笔墨勾勒了诗歌“构陷性”阐释的脉络,并呈现了新旧两党士人利用这一阐释方法相互攻讦的整体面貌,而不是仅就“乌台诗案”或“车盖亭诗案”呈现单方面的史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王安石系年明确的晚年作品中确乎能体现出他与神宗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元丰初期的一些作品,不能简单地以诗体传统来解释,有关这一问题,朱刚、张弛《“元丰行”与晚年王安石的创作焦虑》(《山西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的讨论就相当值得重视。
通篇看来,本书关注的五个问题都是王安石研究史上的经典问题,每一章的讨论对象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先行研究积累。特别是第一章和第五章,取径较为传统,在结论上并未超出内山精也的研究。不过,本书细密的史料罗织足以体现作者深厚的学养,读之令人感佩。同时,本书最终指向的也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给问题为何出现寻找一个解释,这种视角对应的正是本书标题中的“诗歌文化”(poetic culture)。整部大著的努力就是要“置王安石于宋诗史中”(273页),在唐宋诗歌转型的长线索中为王安石的写作和批评寻找锚点,从而超越宋代以降用王安石“强辩”的性格特点解释王安石写作的粗放判断。作者在本书的《尾声》引用刘克庄、方回与袁桷等人的观点,再次指出了王安石诗史定位的复杂性,王安石的诗作一方面在诗句化用和体式偏好上呈现出对唐代诗人的高度承袭,一方面又在技法上早于苏、黄地展示出了典型的宋诗风格。作者最后用全祖望的阐述指明了王安石诗史定位的“过渡人物身份”,也再次坦承王安石诗歌的丰富与变化“使人无法死板地从分期或风格的角度来界说他在宋诗史中的地位”(285页),这也能够印证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一文中认为王诗“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体现了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的整体判断。
本书尚有一些细节上的未尽之处,如本书尽管多次引及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但在第五章没有引述汤氏对《君难托》性质的认识。此外,中译本将乐府诗的两句称为“联”(如231页),也不符合中国古典诗体的惯例。不过这些细微的失误不影响本书的价值。比起作者以方法和视角见长的前作《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本书对编年史、笔记、目录、文集等各种史料的丰富采撷,以及脚注中对次要信息的详尽介绍,都体现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意识与扎实的文献素养。特别是作者对王安石中、英语言先行研究的详备引述,使得本书俨然成为王安石诗歌研究的文献指南。总之,在王安石诗歌研究亟待深入的今天,本书对王安石相关史料的广泛搜求与深密编织,足以令本书成为今后王安石诗歌研究者不可绕过的作品。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