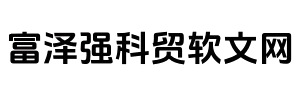刘小朦评《一虫一草游世界》︱跨界的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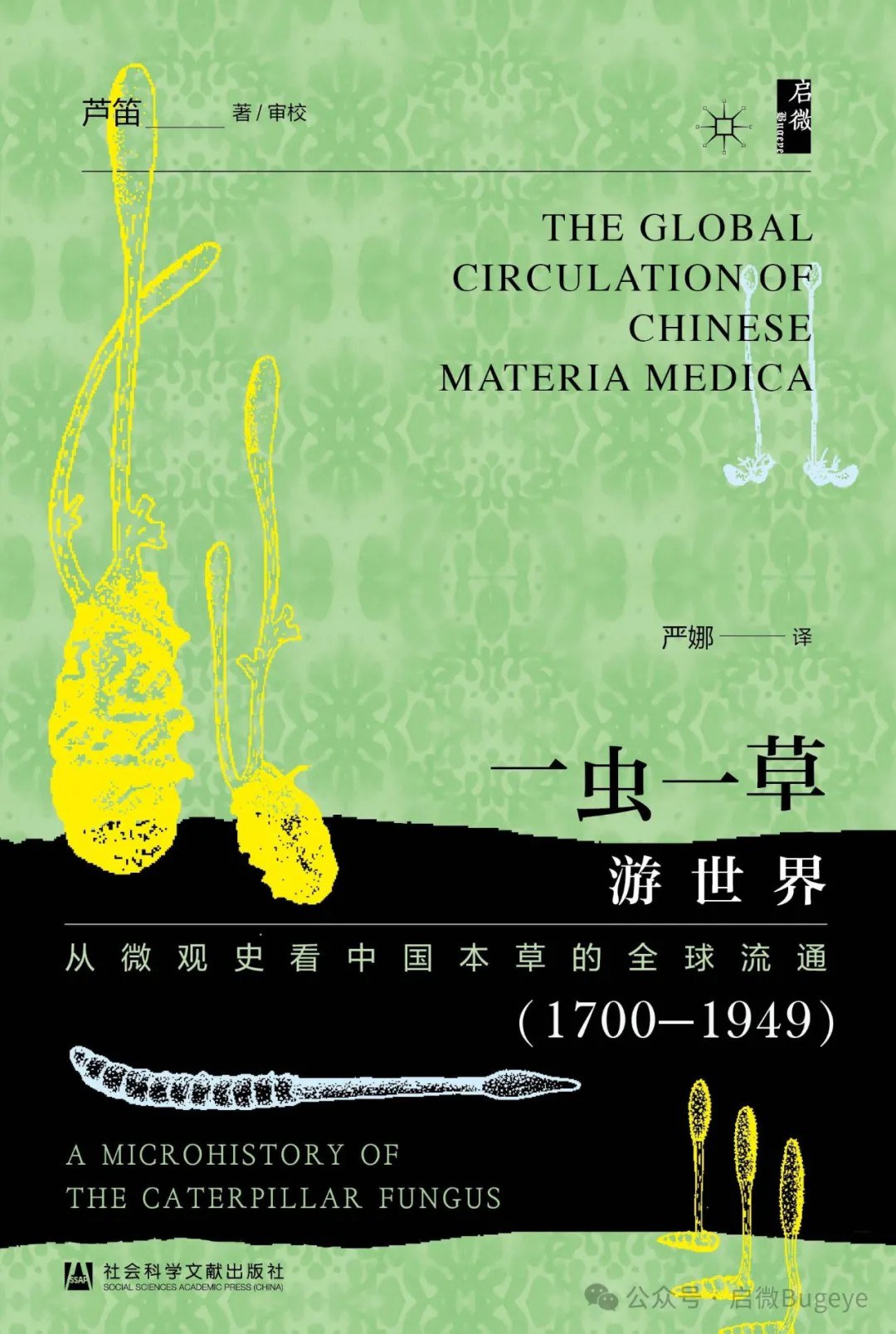
《一虫一草游世界:从微观史看中国本草的全球流通》,芦笛著,严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352页,79.00元
药材多川产,冬虫夏草奇。
一茎细领略,根蒂相维持。
秉性治痨瘵,险症竟能医。
渡江枳化橘,入水雀变蜊。
其理无难解,格物根致知。
道光末年,山东举人张香海宦游川地,在成都写下了这首《草变虫》。诗句本身并不难理解,虽然信息并不完全准确,但其中也涵盖了这种奇异药草的产地、外形、疗效乃至其在不同物种间转化的特征。到了十九世纪,许多在西南地区为官或行旅的士人都听说了这种神奇的药材;它同样随着商品贸易传播到了富庶的江南,成了补虚灵药与馈赠佳品。比张香海稍早的云南诗人戴淳亦曾以之为题赋诗,其中提到“丽江土美有异产,神农当日所未收”。是的,冬虫夏草在中国医学史上并非多么历史悠久的药物,不要说《神农本草经》,甚至在明代的《本草纲目》中也无迹可寻。正因如此,汉文文献中对冬虫夏草的记载并不丰富,难以想象可以支撑起一部专著的体量;此外,冬虫夏草虽然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海外的知名度并不高,那如何以此为题书写一部药物流通的全球史呢?
初见芦笛新著《一虫一草游世界》时,我的心中是有不少疑惑的。但展卷细读,却被其流畅的行文、丰富的资料与精彩的分析所折服。该书使用的材料极为丰富,涵盖了汉、藏、英、法、拉丁、俄、日等多种文字,可以说几乎穷尽了关于冬虫夏草的各类历史材料;作者也熟稔中西科学史、医学史领域的重要成果,在行文中信笔拈来。从一根小小的虫草出发,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十八世纪以来药物在不同地域与文化间的流转、横跨欧亚大陆的自然知识网络的形成以及医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本书的特色,我想没有比“跨界”更合适的词汇:冬虫夏草在空间上跨越了地理的疆界、在形态上跨越了物种的界限、在使用上跨越了食与药的差异、在知识上跨越了不同医学体系的区隔。在这样一种跨界的药物背后无疑有着精彩的故事,借助作者的生花妙笔,冬虫夏草的历史也跨越时空与现代读者相遇。
本书的四个章节大致以时间顺序为轴,亦有着清晰的脉络。第一章讲述冬虫夏草的藏医起源,并随着贡赋、贸易和人际网络传入汉地,被中医药体系纳入本草之中,成为一种在疗效和价格上都堪比人参的药品。第二、三章是本书的主体,重点勾勒冬虫夏草经由传教士、博物学者、探险家、贸易商等途径传入欧洲和日本的历史过程;它在十八、十九世纪被纳入新的分类学体系和科学医学的认知体系之中,传奇色彩被逐步祛魅,在现代科学体系下完成了“客观化”的进程。第四章则将视角转回中国,中西医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碰撞影响深远,在近代科学强势的话语体系与认识论框架之下,冬虫夏草的新知在中国逐步传播,成为中医药现代化与科学化进程中的一个有趣案例。从谋篇立论的侧重点来看,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化史作品,它带有极为浓厚的科学史色彩。
在全球科学史领域,博物学无疑是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各类商品在新旧大陆之间的频繁流动塑造了历史学者所称的“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在这些商品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各种自然产物:既有咖啡、茶叶这些成瘾性饮品,也有土豆、玉米等来自新大陆的农作物;既有金鸡纳树皮、土茯苓这类药材,也有胭脂虫、靛青等染料;既有棉花、丝绸这些纺织品,也有烹饪中必不可少的各类香料。这些动植物产品在经济史的脉络下是全球贸易中商品流动的个案,在物质文化史视角下是改变日常生活、塑造社会阶层与文化区隔的消费品。科学史则关注近代早期不断涌入欧洲的自然产物和知识对科学形成的重要性,强调近代科学不仅仅是西欧一隅的思想成就,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牛顿需要依赖来自南美和西非的观测数据来发展万有引力定律,林奈也只有通过欧洲广阔科学网络搜集的动植物标本才能完成奠定现代分类学基础的著作。在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中,欧洲以外被视为“无科学”之地,只能提供“原始材料”;而欧洲则是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或者拉图尔所说的“计算中心”,通过观察、实验等手段不断积累着科学事实。如今的科学史研究则越来越重视欧洲以外的本土知识,这些知识不再被视为落后愚昧的迷信;与科学一样,他们同样也是深刻嵌入社会文化情景中的认识论体系,在认识、利用与改造自然中有着独特的意义。
冬虫夏草便可在此脉络下得以理解。如果以科学进步主义的叙事来看,对冬虫夏草的认知从物种间相互转化的奇观逐渐演变成菌丝感染蛾科幼虫的科学事实,这一演变是在欧洲完成的,并在近代传入中国。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单线进步的发展,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尽管冬虫夏草最终在欧洲被祛魅,但最初吸引欧洲旅行者和科学家目光的无疑是其跨物种的奇妙形态与汉藏医学传统中建构的神奇疗效,而这些也成为冬虫夏草的分类学与科学研究的起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侧重点:在中国,它被当作堪比人参的名贵补药,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其药用价值和作为礼品的社会功能;在日本,这种贵重药品的商业价值激发了他们探索冬虫夏草本土化的兴趣;在欧洲,冬虫夏草的医学价值并没有得到承认,反而成为分类学与昆虫学研究中争议的焦点。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知识网络中,不同知识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平等。尤其在十九世纪之后,科学随着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逐步在全球扩散,欧洲建构的科学事实也随之成为支配性的解释体系。东亚社会对冬虫夏草的传统认知仍然存在,但被逐出了科学领地,成为传统医药和商业中流传的“神话”。在此,我不禁想起了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中提到关于松茸科学研究中两种几乎相反的解释模式:日本研究者注重松茸生长的整体环境及多物种间的共生,认为恰当的人类干预有利于扭转松茸减产的趋势;而美国研究者则将松茸资源的减少归咎于人类的过度采摘,因此人类的干扰应被严格限制。这两种不相容的科学解释模式共存的状态也提示我们在当代林业科学中所摆脱不了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对冬虫夏草的研究,东亚社会与历史中是否可总结出与西方科学里客观化趋势不同的认知方式呢?这或许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作者对史料搜集用功极深,尤其对海外多语种史料的运用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提示中国本草史的研究者拓宽视野,从域外史料出发探索更为广阔的药物全球史。不过,从作者的叙述可知,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人对冬虫夏草的兴趣更多体现在科学研究之上;它并没有对西方医学发展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也从来没有被大规模进口到欧洲。从西方医学与商业的角度来看,冬虫夏草的地位似乎并不突出。在全球流通的更多是关于冬虫夏草的知识,而非冬虫夏草本身。这种现象无疑可以成为“无知学”(Agnotology)的典型案例。隆达·施宾格在《植物与帝国》中探讨了原产美洲的金凤花,它虽然早为欧洲科学家所知,且有着多项实验成果,但它并未作为堕胎药在大西洋海域间自由流通。这一现象与近代早期欧洲的性别政治密切相关。那冬虫夏草为何未被欧洲人采用呢?或许栗山茂久对人参在欧洲境遇的解释可以被挪用到冬虫夏草的案例之中。十八世纪之后,欧洲制药学开始重视化学制剂,传统的草药研究逐步衰落;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传统医学中对“过剩”的恐惧使得欧洲人更偏好“泻药”而非“补药”。当然,冬虫夏草的案例与人参是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讨论冬虫夏草在海外的传播时,作者旁征博引,将冬虫夏草研究放到西方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兴趣与探索的大背景下进行描述与阐释。相较之下,本书对于冬虫夏草在清代中国传播的描绘却略显单薄。尽管从地域而言,冬虫夏草确实是一种源自中国的药品;但从医学体系来看,它却是在十八世纪从藏医学新进引入中医传统本草体系的药物。为何这一时间节点如此重要?作者敏锐指出了清朝对西部的军事征服在冬虫夏草东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章结尾部分提到:“中国关于虫草生产的信息越来越多,不仅涉及经济和医学问题,还涉及族群中心主义、对帝国的拥护及对异域空间和自然的想象。”这一论断鞭辟入里,但在第一章却更多集中在知识论层面的讨论,较少体现政治层面的影响。
冬虫夏草虽然特别,但它也是清代药材贸易体系中逐步增长的边疆药材之一。清代边疆药材知识的显著增长,无疑与清朝疆域的巩固密切相关,也与考据学者对边疆史地日益增长的兴趣有显著关联。具体到冬虫夏草的产地,自雍正以来的改土归流使得越来越多的汉地官员及其幕僚进入这一地区,他们亦是记载与传播当地土产药材的重要力量。本文开篇提到的张香海便是其中一例,晚清朴学名家俞樾也曾收到来自四川友人馈赠的冬虫夏草。边和在对《本草纲目拾遗》的研究中指出,赵学敏作为流寓幕客的身份让他得以接触到多样的药品实物与知识。这类下层士人——或者说“小知识人”——在清代本草知识生产中似乎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记录冬虫夏草及其他药物知识的官员、旅人、商贾、医生等群体是否也构成了一个堪比同时期欧洲帝国的知识与信息流通网络呢?我们当然不能贸然下此结论,不过这也提示我们思考:对于中国本草的全球史研究,到底是为全球科学史做一注脚,还是应该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抑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历史在全球史中的定位。
当然,以上仅是我通过阅读此书产生的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作者的材料与框架足以支撑起一部优秀的作品。如今中国的本草与药物史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囿于中文文献,此书的翻译出版显得尤为可贵,它不仅展现了西文文献信息的丰富多彩,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诸多海外科学史领域的经典研究。稍显的遗憾的是,本书没有配备插图。作者在书中重点讨论了关于冬虫夏草的图像呈现,并与欧洲科学图像研究中讨论的 “忠于自然”(true-to-nature)与“机械客观性(mechanical objectivity)”两种认知德性进行比较。但缺少相应的插图,难以给读者直观的感受。虽然封面设计加入了冬虫夏草的历史图像,但其艺术和审美考量并不能完全呈现其中丰富的历史与知识信息,亦无法与文字进行对应。或许在未来再版时,作者可考虑加入插图以弥补缺憾。
作者在后记开篇便引用了庄子的名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表达自己对研究草木虫鱼之历史的志趣。大约在两百年前,云南诗人戴淳在《冬虫夏草》一诗开篇中也化用了庄子的名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蟪蛄何知春与秋,朝生夕殒菌易休。
世间微物类如此,暂寄大块真浮沤。
岂知天地至莫测,难将物理齐庄周。
坚木生蠹质渐化,腐草为萤机常流。
……
清代文人常常将冬虫夏草的转化能力与庄子对世间万物生生化化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作者芦笛与诗人戴淳皆以冬虫夏草作题,以庄子之语寄兴,这也不失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吧。